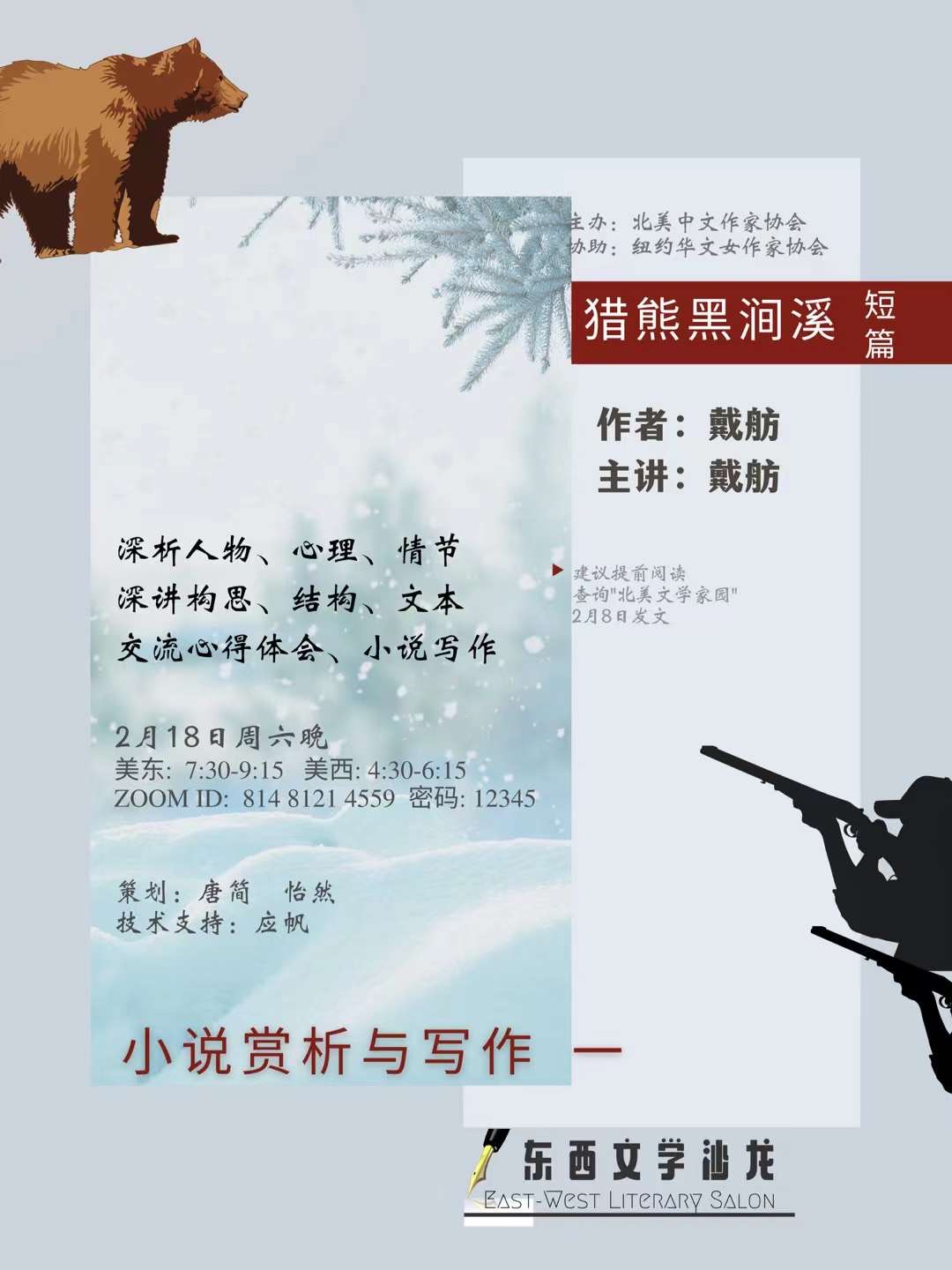转发, 版权属于原作者
那一天,我照常开始了居家网上工作。手机屏幕上弹出了朋友发来的一连串的信息,单位邮箱里也不停有邮件进来。我没时间去关心这些,网上工作会议马上要召开。
开会的惯例是寒暄问候,没想到同事心直口快地说:“文迪,你儿子的学校上了美国大小媒体的头条。“我说:“什么?怎么回事?“同事说:”那个大学是全美第一个主要大学宣布要秋季重开校园的,媒体上都炸了。“听了此话,我再也没心思把会开下去了。查了查手机和邮件,大家都在把这个消息转给我,原来一早这么忙,是有事情发生!
接下来的一个月,秋季回不回大学去上学在我们的家庭会议上讨论了几次。儿子很坚定,一定要按时回去上学。他的理由很简单,困难的时候,他要和他的朋友们在一起。当妈的口里说,一切由儿子决定,心里却有一万个不舍。当我们对新冠疫情没有清醒的认识,我们是冒集体感染的风险让他回去,还是勉强让他留下休学一年呢?一个月里反复几次的家庭会议都没有能说服儿子,他回印州的学校去了。
时间转到二零二零年的十二月,斯城的疫情已经很严重,第一剂新冠疫苗在华州推出。华人社区里有大量的反馈希望有关于疫苗的进一步讲解和知识。斯城华协主席伟玲紧急联络理事会,希望有人能联系到专业医疗人士或组织为华人社区答疑解惑。我作为副主席主动承担了这项任务。但是事情并不顺利。在联络了医生朋友,县卫生署之后,得到的回答都是我们目前人手紧缺,没有余力去社区开展宣传。
几经辗转,我与县卫生署的新冠健康平权小组取得了联系,并被邀请参加他们的定期会议。答疑解惑的专题讲座没有组织成,但是华协可以通过这些定期会议把社区的需求和州里,县里的最新社区服务资源双向转达。
在其中的一次会议上,我代表华协理事会向前来征求意见的州里卫生部的官员大声疾唿:新冠疫苗的相关资料应该有多语种的翻译,非英语的居民有语言障碍,信息无法及时准确的传递出去,有些人因为不懂英语而感染新冠失去生命。此后,不到一个星期,我们收到州里的回复。依据我在会议上的反馈,州里询问应该优先翻译资料为哪几种语言。伟玲主席回复说应该以少数族裔人口决定优先权,西班牙语和中文的使用者为最多。两周之后,州里根据数据分析和我们的反馈,在三十种语言里,优先将新冠有关资料译为西班牙语,中文,俄文,和马绍尔文。我们的声音,为更多的少数族裔以平等机会取得新冠信息、挽救生命做出了贡献。
我把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转达给了华协理事会,也告诉了远方的儿子。他在电话里说:“妈,我真为你们高兴。我们在学校里也互相鼓励互相帮助,我们要共渡艰难时刻。”
此后,我不断在工作之余,义务把与社区健康有关的信息翻译成中文,传递给理事会和华人社区。
二零二一年四月的一个周五傍晚,距离儿子大学毕业只有一个月了。再过一周,儿子的学校安排了集体打新冠疫苗。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。我在电脑上写着一周工作总结。儿子打电话来,我照常嘻嘻哈哈:“儿子,你又想我了?”电话那边,他轻轻地说:“妈,我新冠检测阳性,在学校隔离区隔离。”我沉默了,顿了顿,强装镇静说:“你没事吧?一般症状都会很轻。”“整个宿舍都得了,应该没问题。”他说,似乎比我还镇定。儿子宿舍里有六个学生,一位医学院的预科生因为在医疗机构做义工,提前打过新冠疫苗,没有被感染。剩下的五位在两周里前后感染新冠病毒。他们症状各自不同,而且在公共健康部门追溯感染源的询问中,没有找到初始感染源。也就是说,在他们都极度小心,采取了防范措施后,不知道谁从哪里感染了病毒。从交谈中,我感到了儿子的沮丧和无助。听着儿子的讲述,我的心不断下沉。
整个周末,儿子的状态越来越差,他常常昏睡,要靠我打电话叫醒提醒喝水吃饭。周六晚上,在绝望中,我写了长邮件给单位,交代了工作,说我要赶往印州儿子那里。但是老公和儿子坚决不让我去,因为儿子在隔离区,我即使飞过去也是见不到他的,而且路上有可能被传染上新冠病毒。此时的我,不论老公,朋友怎么安慰,我都只有活不下去的感觉。无奈中,我从网上订了食品和鲜花发给儿子,每天每两小时打给他问他的情况,准备了儿子学校就近的医疗设施的名单以备急用。如此心急如焚而又鞭长莫及地过了几天,他说他失去了味觉和嗅觉。即使如此糟糕的情况下,儿子还是只要醒着,就在赶作业、上网课。他说他要忙着完成功课以驱赶负面情绪,而且要按时毕业,在他的学校医生、护士和教授们鼓励下,他是如此坚强。
此时,学校发布了五月毕业典礼的草案,要缩小庆祝规模,一个家庭只有两个成员可以取得典礼的入场券,而且要求这两个人都打过新冠疫苗。在这令人煎熬的日子里,我天天都会对儿子说:“你要好好休息,等我们去参加你的毕业典礼。”其实,我并不确定,是否还可以与他再次相见。
十天后,儿子在舍友中最先转好了。二十天后,儿子和他的舍友们幸运地完全恢复了健康。
仿佛儿子的高中毕业还在昨天。这四年里,我们三次去学校探访。其中两次,都是在疫情的影响下在去与不去的两难之中,我们选择了去。我的心此时已经飞往了印州小镇,我要揽住儿子宽厚的肩膀,仔细端详他,找出病痛留下的痕迹,用温暖的手抚平它。我要写下我们的祝福,让父母之爱在他的身边。
五月底,儿子以优异成绩取得了双专业的本科毕业。我和老公提前打好疫苗,戴着口罩,转了两次机飞去参加毕业典礼。飞机上满员,虽然在飞机上我们不敢摘下口罩吃喝,但是看到很多人穿戴着有儿子学校标志的衣服,我们心中的喜悦和温暖抵消了旅行中的恐惧。很多坐在附近的人互相问候,分享着自己孩子的姓名,专业。还有人向我们打招唿,祝我们远道旅行愉快。漫长的旅途中,我写下了给儿子的一封信:
……
你是一个很棒的人,这是首要的。你有温和的心,关心别人,这非常难得。你勤奋努力追求梦想,但又接受任何后果。
……
飞机落地的那晚,毕业式举行了。夕阳余晖下,全美着名的橄榄球场上聚集着带着口罩的年轻人,他们生气勃勃,载歌载舞。一同经历了艰难时刻的大学毕业生们是如此难舍难分。儿子帮朋友理好毕业礼服的领子,把自己的饰带戴在这个买不起饰带的男孩的肩上,拍着那个男孩的肩膀说:“该你上场了,我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,为你自己骄傲!你妈妈在直播里看见你,也一定为你骄傲!”我们在人群中赞许地默默微笑。